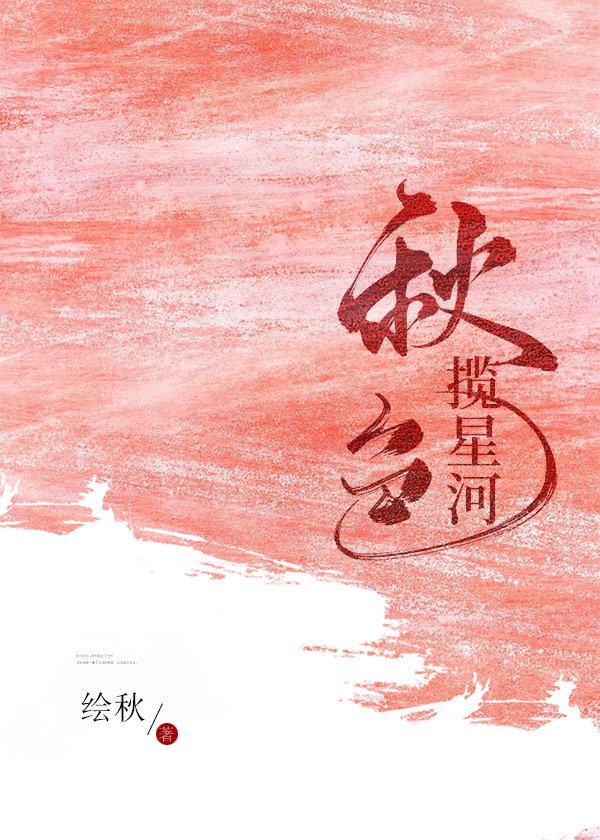六零小说>蝉鸣坠雪时 > 锋芒藏鞘温雅生威(第1页)
锋芒藏鞘温雅生威(第1页)
晨雾尚未散尽,夏氏集团顶楼的会议室已泛着冷光。长条会议桌的尽头,夏栖迟指尖轻叩着文件边缘,骨节分明的手在晨光里透着瓷白,与黑檀木桌面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桌旁坐着的几位董事大气不敢出,那份关于生物基地扩建的方案摆在面前,墨迹未干的签名处,“夏栖迟”三个字笔锋凌厉,却在收笔处带着不易察觉的圆润——那是冬以安说“签名别太硬,像在发脾气”后,他特意改的。
“霍氏的违约金,按合同三倍赔付。”夏栖迟的声音不高,却像块冰投入滚油,瞬间炸开。他抬眼时,目光扫过主位旁的空位——那是夏明远的位置,今早临时让他代为主持。“他们用我们的专利边角料做劣质香氛,砸的是夏氏的招牌,这点钱,买个教训。”
二伯夏明诚捏着钢笔的手紧了紧:“小少爷,这样会不会太刚?霍家在北方的渠道……”
“渠道可以再铺,信誉碎了,捡都捡不起来。”夏栖迟打断他,指尖翻开方案的附件,里面贴着冬以安手绘的香氛分子结构图,粉色的樱花与绿色的薄荷缠绕成链,“我们要做的是‘共生’,不是‘苟合’。”
他把方案推过去,纸张与桌面摩擦的轻响,竟比拍桌的怒斥更有分量,“下午三点前,我要各位的签字,逾期视为弃权。”
散会时,董事们鱼贯而出,经过夏栖迟身边时都下意识放轻了脚步。有人偷瞄他握着钢笔的手——那只在实验室里给樱花苗换土的手,此刻捏着笔的力度,竟让笔杆微微泛白。只有老管家知道,今早出门前,冬以安替他擦钢笔时说:“别太用力,笔会疼的。”
夏栖迟望着窗外,晨光正漫过樱花园的顶,实验室的玻璃罩在雾里泛着浅蓝。他拿出手机发消息:“中午回不去,替我给薄荷浇点水。”
很快收到回复,是张照片:冬以安蹲在花房边,手里举着水壶,薄荷叶片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光,配文是“它说等你回来吃樱花酥”。男人的嘴角不自觉地软下来,刚才在会议室里凝结的冷霜,仿佛被这张照片融成了水。
中午的商务宴请设在湖心亭。红木圆桌旁,合作方代表王总正唾沫横飞地讲着笑话,眼角的余光却始终瞟着夏栖迟——这位夏家小少爷,听说常年泡在实验室,今日一见,才知传闻有多离谱。他穿着烟灰色西装,袖口挽到小臂,露出的银镯子与腕表形成奇妙的和谐,听笑话时唇角噙着浅淡的笑,既不显得敷衍,也不过分热络,像幅留白恰到好处的水墨画。
“夏少年轻有为啊,”王总端起酒杯,“听说您亲自研发的香氛,连法国那边都来询价?”
夏栖迟抬手示意服务生添茶,青瓷杯沿沾着他的指温:“不是我,是我和我爱人一起。”他提起冬以安时,眼里的光忽然亮了些,像落了星子,“他对薄荷的理解,是天生的。”
王总愣了愣,没想到他会如此坦诚。寻常富二代谈及合作,总爱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,这位却在酒桌上,把“一起”两个字说得郑重。
“尝尝这个。”夏栖迟夹了块水晶虾饺,放在王总碟中,“这家的虾饺用的是晨露虾,和我们的‘共生’香氛一样,讲究一个‘鲜’字。”他没提合作细节,只聊食材的产地、火候的拿捏,说到兴起时,甚至能报出虾饺皮的面粉与水的精确配比,像在念实验数据。
王总越听越心惊——这人哪里是不懂商场?他是把实验室的精准,用到了待人接物里。每句话的分寸,每个动作的轻重,都像用天平称过,既让人舒服,又暗暗透着“我很专业”的底气。
宴席过半,王总主动谈起合同:“夏少,你们的方案我看了,溢价五个点,我签。”
夏栖迟抬眉时,睫毛在眼下投出浅影:“王总不砍价?”
“砍不动。”王总笑了,指着他腕间的银镯子,“您连戴镯子都这么讲究——既不摘下来显得刻意,也不藏起来显得怯懦,这份从容,比合同上的条款更让人放心。”他顿了顿,“何况,能把研究做得这么细的人,做生意不会差。”
返程的车上,夏栖迟摩挲着银镯子,冰凉的金属下,仿佛还带着冬以安替他戴上时的温度。老管家递来份文件:“苏夫人让人送来的,说这是当年她和先生谈成第一笔合作时的记录。”
文件里夹着张泛黄的便签,上面写着:“谈判不是比谁声音大,是比谁更懂对方的痒处。他要利,你给利;他要名,你给名;他要尊重,你就把姿态放得刚刚好,让他觉得赢了面子,你得了里子。”
夏栖迟忽然想起今早冬以安的话:“薄荷之所以清凉,是因为它知道什么时候该收敛气味,什么时候该释放。”原来所谓的继承人魅力,从不是锋芒毕露,是像薄荷一样,把刺藏在叶片深处,待人需要时,才透出恰到好处的清冽。
下午的股东临时会议上,夏明诚带着几位元老发难,质疑生物基地扩建的预算过高。“小少爷只懂实验室的瓶瓶罐罐,哪知道建材市场的水深?”有人拍着桌子,“这预算单,怕是被人坑了!”
夏栖迟没急着反驳,而是打开投影仪。屏幕上出现的不是枯燥的报价表,是他亲自去建材厂拍的视频:工人正在切割樱花木,镜头扫过木料上的年轮,他的声音适时响起:“这种木材防腐性强,比普通松木贵三成,但能用二十年,折算下来每年成本更低。”画面一转,是冬以安在实验室里测试木材的香氛吸附性,“而且它能吸附‘共生’香氛,让基地的每个角落都有樱花味——这是免费的广告。”
视频的最后,是冬以安对着镜头笑:“夏总说,要让来参观的人,一进门就觉得‘啊,这很夏氏’。”
会议室里静了静。那些准备好的刻薄话,忽然像被戳破的气球,泄了气。他们看着屏幕上笑得眉眼弯弯的年轻人,又看看主位上从容淡定的夏栖迟,忽然明白,这位小少爷的底气,从来不是夏家的姓氏,是他身边有个人,能让他把冰冷的商业计划,都镀上点人情的暖。
夏明诚的脸青一阵白一阵,最终在方案上签了字。散会时,他经过夏栖迟身边,低声说:“你比你爸狠。”
“我只是比他懂,什么该守,什么该放。”夏栖迟起身时,西装下摆扫过椅子,带出的风里,仿佛还带着实验室的薄荷香,“爸守的是夏氏的疆土,我守的是夏氏该有的样子。”
夕阳西下时,夏栖迟推开实验室的门。冬以安正趴在操作台上睡觉,脸颊边放着块没吃完的樱花酥,嘴角沾着点粉白的屑。恒温箱里的晚樱开得正盛,粉白的花瓣落在他的发间,像撒了把碎雪。
夏栖迟走过去,蹲在他身边,指尖轻轻擦去他嘴角的酥屑。动作温柔得像在给幼苗除虫,与白天在会议室里那个眼神凌厉的继承人判若两人。
“回来啦?”冬以安迷迷糊糊地睁眼,看见他腕间的银镯子,伸手就去碰,“今天没吵架吧?”
“没有,”夏栖迟把他拉起来,让他靠在自己肩上,“他们说我比爸狠。”
“才不,”冬以安往他怀里缩了缩,闻着他身上的雪松混着樱花酥的甜,“你是比他温柔,才让人舍不得跟你吵。”
香氛仪换了“暮归”配方,是用夕阳下的樱花与薄荷蒸馏的,雾气里带着点慵懒的暖。夏栖迟看着恒温箱里交缠生长的植株,忽然想起苏婉说的话:“真正的领导力,不是让人怕你,是让人信你——信你的专业,信你的人品,信跟着你,能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样子。”
他低头吻了吻冬以安的发顶,声音轻得像雾:“以前总觉得,继承人的魅力是权力和财富,现在才懂,是能让你安心做研究,让张妈放心烤樱花酥,让反对你的人最终说‘你是对的’——这种能把身边人护得很好的能力,才是最该继承的东西。”
窗外的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,交叠在实验室的地板上,像株共生的植物。冬以安忽然想起今天王总说的话:“夏少的魅力,在于他把‘夏氏继承人’这个身份,活成了‘夏栖迟’自己。”
是啊,他没有变成冷冰冰的商业机器,没有被家族的规矩磨掉棱角,而是像块被时光细细打磨的玉,既保留着实验室里的温润,又透着商场上的清辉。那些看似矛盾的特质——温柔与锐利,坦诚与城府,随性与礼节——在他身上融成了独特的光,让人远远看着,就知道这是夏栖迟,是那个会在雪地里烤红薯,也能在会议室里镇住全场的夏栖迟。
深夜的实验室,香氛雾在月光里轻轻流动。
夏栖迟抱着冬以安躺在床上,听着他平稳的呼吸,忽然觉得,所谓的继承人魅力,从来不是天生的,是被爱与责任慢慢焐出来的。就像那枚银镯子,起初带着金属的冷硬,被两人的体温焐久了,也变得温润贴心,既能在宴会上衬得起西装,也能在实验室里,与薄荷的叶片轻轻碰撞,发出温柔的响。
而他,会带着这份被爱浸润的魅力,把夏氏的疆土,种满樱花与薄荷,让每个走进来的人都知道,这里不仅有冰冷的合同与数字,还有滚烫的真心,和把日子过成诗的勇气。
和心爱的人在一起,是夏栖迟执着了一次又一次而这一生身边的人是温热的,不是那个冰冷的尸体,他早已心满意足,他把冬以安搂的更紧了,这样子他就不会离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