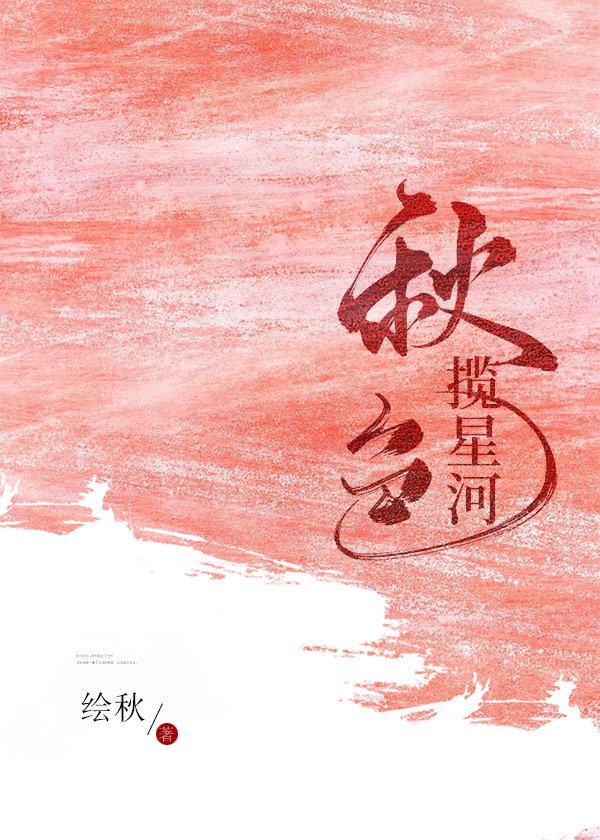六零小说>忒修斯上 > E72(第2页)
E72(第2页)
那日夕阳鎏金,绣楼上的高小姐悄悄透过花木窗,第一次看见未婚夫的背影。年轻的小侯爷一袭素净黑袍,落子时袖口露出半截缠着孝带的手腕。将门之后,仪态却尽显矜贵沉稳之态。
“琴案上的白露琴忽然有了温度。我的指尖流出一段新谱的调子,那是想弹给他听的《枕云眠》。”
当晚父亲转交给我一样东西,素白信笺上笔力遒劲的字迹,竟是他的信,父亲竟允许了?后来才知,是未婚夫说服了父亲。
“这不合礼数。”
“既已定亲,通些书信也无妨,总好过婚后相见如路人。”
"到底是老侯爷教养出来的,少年人只盼忠君报国。"高老夫人最是欣慰。她敬佩老侯爷的为人,更满意这个在丧亲之痛中仍不忘礼数的女婿。君子六艺俱佳,却不骄不躁;身为侯府独苗,却洁身自好,婚事虽一拖再拖,却对女儿愈发情有独钟。偶尔托她转交的信笺,字里行间都是克制的衷情。
老夫人摩挲着嫁妆单子,心想再添两箱上好的棋局茶盏——这样好的女婿,值得女儿多等三年。
“女家要把新娘余生从穿到用的一切都想打贴妥当,嫁妆无外乎是,木质家具、床上用品、四季衣着、杯盘碗碟、铜漆烛器、金银首饰、珍爱物件这七类。每件每样都要成双对,夫唱妇随,从一而终。”
---
变故发生在二十岁这年。那一天也如今日这般,春寒料峭,雪过天晴。
清晨,司宁梳妆前,又翻开随身戴的香囊,取出一方沾碎纸片的帕子。
“展信舒颜,见字如面。”少年时那些翘首以盼的日子,泛着淡淡的墨香,在纸页翻飞间悄然流逝。不知不觉,高小姐与陆公子往来的书信在书案上对的越来越高。
“除了书信,他曾赠予我许多其他物件。但是如今留下来的只有这生锈的字迹,也是最后一件和他有关的东西。”
这一年,风雨飘摇,朝堂不容乐观,血色残阳刚坠下城楼,兵部加急文书已砸在忠勇侯府的正堂,而高府收到了一封冷情的退婚书:
"□□卿卿:"
"见字如面。陆某此去,恐负海棠之约。今退还聘定之佩,若事有不谐,望勿以为念。小姐青春正好,莫负终托。"
二更梆子敲过第三响。
高府西墙外,陆□□的衣衫覆满夜露。他盯着绣楼那扇雕花窗,三次抬手,三次又放下。最终一样东西被他亲自系在窗外海棠枝上,像退婚书上的寥寥数语般仓促离开。
墨迹未干的宣纸缀在另外半枚鸳鸯鱼玉佩上随风在花间飘摇——绣楼主人开窗就能看见。
“那晚每一刻钟都在敲打我的神经。五更鼓响,我被军号声惊醒。枝头飘荡的丝绳砸碎了完整的晨曦。我抱起琴,不管不顾的奔上高台,向着城门的方向,奏响了曾挑灯夜弹的《枕云眠》。”
琴声没有回响,队伍终究没有回头,他们渐渐消失在晨雾里,黄土中。
我们曾一窗之隔。
同年深秋,敌军破城。
那天丫鬟惊慌地跑来:"小姐,不好了!叛军攻破了东门,老爷让你随夫人立刻出城!"
绵州有师傅接应。这样想着我们扮上男装混进流民中,踏上了前往绵州的逃亡之路。
可母亲病倒了。那个雨夜她拉着我的手说:"□□,你记住,无论遭遇什么,都要活着。。。活着等陆小侯爷回来接你。。。"
接下来的日子如同噩梦,命运步步紧逼。不知谁泄露了风声,我被从绵州的师傅家里挖了出来顶替,师傅的手在我掌心渐渐冰凉。我才脱下外衫盖在师傅脸上,就被拖走了。
父亲被斩于市曹,母亲病逝异乡,害死恩师的我沦为官婢,因识文断字,被分派到织造局记账。后织造使看中我的才貌,将我卖给了最负盛名的青楼"会仙楼"。
二十二岁那年,我用我的顺从、琴声、诗词和若即若离的态度周旋于各色客人之间。这封不值钱的信笺一直跟着我兜兜转转,期间虽吃了许多苦头,幸而最终回到了家乡。海棠花依旧,不见楼上故人影。
上面没有称呼,没有落款,只有两行力透纸背的字被我绣在帕子上:
"敢赴三军百战死,勿诺千金无尽愁。"
又是多少年过去了,连字迹都凋零的岁月,如这陈年刺绣般的我,还要行尸走肉多久?
青丝未系同心结,白骨先成异乡丘。死者壮烈,生者当决绝。未嫁之人,未亡之名。尔赴国殇,我守国丧。
反正我成了会仙楼最红的姑娘。客人们赞我冷艳高贵,不像风尘女子,倒像哪家落魄的千金小姐。他们不知道,他们说的没错。
每逢初春,会仙楼都会缭绕着走不出的曲调。
日复一日,年华虚度。司宁不止一次的怀念年少时窗外那道未曾谋面的身影,他会在明天来见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