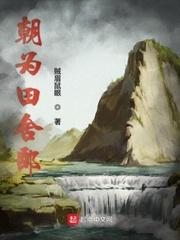六零小说>日常生活颂歌 > 只想缓缓走着看沿路的景色(第3页)
只想缓缓走着看沿路的景色(第3页)
好些年前我译过一册《狂言十番》,其中有一篇也说及撒豆的事,原名“节分”,为通俗起见却改译为“立春”了。这里说有蓬莱岛的鬼于立春前夜来到日本,走进人家去,与女主人调戏,被女人乘隙用豆打了出来,只落得将隐身笠隐身蓑和招宝的小槌都留下在屋里了。有云:
女咦,正好时候了,撒起豆来吧。
“福里边,福里边!
鬼外边,鬼外边!”(用豆打鬼)
鬼这可不行。
女“鬼外边,鬼外边!”
案狂言盛行于室町时代,则是十四世纪也。嵩山禅师居中(一二七七年至一三四五年)曾两度入唐求法,为当时五山名僧,著有《少林一曲》一卷,今不传,卜幽轩著《东见记》卷上载其所作诗一首,题曰《节分夜吃炒豆》:
粒粒冷灰爆一声,年年今夜发威灵。
暗中信手轻抛散,打着诸方鬼眼睛。
江户时代初期儒者林罗山著《庖丁书录》中亦引此诗,解说稍不同,盖传闻异词也:
古人诗中,咏除夜之豆云,暗中信手频抛掷,打着诸方鬼眼睛,盖撒大豆以打瞎鬼眼也。
《类聚名物考》卷五引《万物故事要诀》,谓依古记所云,春夜撒豆起于宇多天皇时,正是九世纪之末,又云:
炒三石三斗大豆,以打鬼目,则十六只眼睛悉被打瞎,可捉之归。
此虽是毗沙门天王所示教,恐未足为典据,故宁信嵩山诗为撒豆作证,至于福内鬼外的祝语已见于狂言,而年代亦难确说,据若月紫兰著《东京年中行事》卷上云,此语见于《卧云日件录》,案此录为五山僧瑞溪周凤所作,生于十五世纪上半,比嵩山要迟了一百年,但去今亦有五百年之久矣。
傩在中国古已有之,《论语》里的乡人傩是我们最记得的一例,时日不一定,大抵是季节的交关吧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云,先腊一日大傩,谓之逐疫。《吕氏春秋·季冬纪》高氏注云,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,谓之逐除。据《南部新书》及《东京梦华录》,唐宋大傩都在除夕。日本则在立春前夜,与中国殊异,唯其用意则并无不同。民间甚重节分,俗以立春为岁始,春夜的意义等于除夕,笑话题云“过年”,即是此意,二者均是年岁之交界,不过一依太阳,一依太阴历耳。中国推算八字亦以立春为准,如生于正月而在立春节前,则仍以旧年干支论,此通例也。避凶趋吉,人情之常,平时忍受无可如何,到得岁时告一段落,想趁这机会用点法术,变换个新场面,这便是那些仪式的缘起。最初或者期待有什么效用,后来也渐渐的淡下去,成为一种行事罢了。谭复堂在日记上记七夕祀天孙事,结论曰,千古有此一种传闻旧说,亦复佳耳。对于追傩,如应用同样的看法,我想也很适当吧。
缘日
到了夏天,时常想起东京的夜店。己酉庚戌之际,家住本乡的西片町,晚间多往大学前一带散步,那里每天都有夜店,但是在缘日特别热闹,想起来那正是每月初八本乡四丁目的药师如来吧。缘日意云有缘之日,是诸神佛的诞日或成道示现之日,每月在这一天寺院里举行仪式,有许多人来参拜,同时便有各种商人都来摆摊营业,自饮食用具,花草玩物,以至戏法杂耍,无不具备,颇似北京的庙会,不过庙会虽在寺院内,似乎已经全是市集的性质,又只以白天为限,缘日则晚间更为繁盛,又还算是宗教的行事,根本上就有点不同了。若月紫兰著《东京年中行事》卷上有“缘日”一则,前半云:
东京市中每日必在什么地方有毗沙门,或药师,或稻荷样等等的祭祀。这便是缘日,晚间只要天气好,就有各色的什么饮食店,粗点心店,旧家具店,玩物店,以及种种家庭用具店,在那寺院境内及其附近,不知有多少家,接连的排着,开起所谓露店来,其中最有意思的大概要算是草花店吧。将各样应节的花木拿来摆着,讨着无法无天的价目,等候寿头来上钩。他们所讨的既是无法无天的价目,所以买客也总是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乱七八糟的还价。其中也有说岂有此理的,拒绝不理的,但是假如看去这并不是闹了玩的,卖花的也等到差不多适当的价钱就卖给客人了。
寺门静轩著《江户繁昌记》初编中有赛日一篇,也是写缘日情形的,原用汉文,今抄录一部分如下:
古俚曲词云,月之八日茅场町,大师赛诣不动样,是可以证都中好赛为风之古。赛最盛于夏晚。各场门前街贾人争张露肆,卖器物者皆铺蒲席,并烧萨摩蜡烛,贾食物者必安床阁,吊鱼油灯火,陈果与蓏,烧团粉与明鲞(案此应作鱿鱼),轧轧为鱼鲊,沸沸煎油糍。或列百物,价皆十九钱,随人择取,或拈阄合印,赌一货卖之于数人。卖茶娘必美艳,鬻水声自清凉。炫西瓜者照红笺灯,沽饧者张大油伞。灯笼儿(案据旁训即酸浆)十头一串,大通豆一囊四钱。以硝子坛盛金鱼,以黑纱囊贮丹萤。近年麦汤之行,茶店大抵供汤,缘麦汤出葛汤,自葛汤出卵汤,并和以砂糖,其他殊雪紫苏,色色异味。其际橐驼师(案即花匠)罗列盆卉种类,皆陈之于架上,闹花闲草,斗奇竟异,枝为屈蟠者,为气条者,叶有间色者,有间道者。钱蒲细叶者栽之以石,石长生作穿眼者以索垂之。若作托叶衣花,若树芦干挟枝。霸王树(案即仙人掌)拥虞美人草,凤尾蕉杂麒麟角(原注云,汉名龙牙木)。百两金,万年青,珊瑚翠兰,种种殊趣。大夫之松,君子之竹,杂木骈植,萧森成林。林下一面,野花点缀。杜荣招客,如求自鬻,女郎花(原注云,汉名败酱)媚伴老少年。露滴泪断肠花,风飘芳燕尾香。鸡冠草皆拱立,凤仙花自不凡。领幽光牵牛花,妆闹色洛阳花。卷丹偏其,黄芩萋兮。桔梗簇紫色,欲夺他家之红,米囊花碎,散落委泥,夜落金钱往往可拾。新罗菊接扶桑花边,见佛头菊于曼陀罗花天竺花间。向此红碧绵绮丛间,夹以虫商。宫商缴如,徵羽绎如,狗蝇黄(案和名草云雀,金铃子类)唱,纺绩娘和,金钟儿声应金琵琶,可恶为聒聒儿所夺。两担笼内,几种虫声,唧唧送韵,绣出武藏野当年荒凉之色,见之于热闹市中之今日,真奇观矣。
《江户繁昌记》共有六编,悉用汉文所写,而别有风趣,间亦有与中国用字造句绝异之处,略改一二,余仍其旧。初编作于天保辛卯(一八三一),距今已一百十年,若月氏著上卷刊于明治辛亥(一九一一),亦在今三十年前,而二书相隔盖亦已有八十年之久矣。比较起来,似乎八十年的前后还没有什么大变化,本乡药师的花木大抵也是那些东西,只是多了些洋种,如鹤子花等罢了。近三十年的变化或者更大也未可料,虽然这并没有直接见闻,推想当是如此,总之西洋草花该大占了势力了吧。
北京庙会也多花店,只可惜不大有人注意,予以记录。《北平风俗类征》十三卷征引非不繁富,可是略一翻阅,查不到什么写花厂的文章,结果还只有敦礼臣所著的《燕京岁时记》,记“东西庙”一则下云:
西庙曰护国寺,在皇城西北定府大街正西,东庙曰隆福寺,在东四牌楼西马市正北,自正月起,每逢七八日开西庙,九十日开东庙。开会之日,百货云集,凡珠玉绫罗,衣服饮食,古玩字画,花鸟虫鱼,以及寻常日用之物,星卜杂技之流,无所不有,乃都城内之一大市会也。两庙花厂尤为雅观,夏日以茉莉为胜,秋日以桂菊为胜,冬日以水仙为胜,至于春花中如牡丹海棠丁香碧桃之流,皆能于严冬开放,鲜艳异常,洵足以巧夺天工,预支月令。
这里虽然语焉不详,但是慰情胜无,可以珍重。这种事情在有些人看来觉得没有意思,或者还是玩物丧志,要为道学家所呵叱,这个我也知道,向来没有人肯下笔记录,岂不就是为此么,但是我仍是相信,这都值得用心,而且还很有用处。要了解一国民的文化,特别是外国的,我觉得如单从表面去看,那是无益的事,须得着眼于其情感生活,能够了解几分对于自然与人生态度,这才可以稍有所得。从前我常想从文学美术去窥见一国的文化大略,结局是徒劳而无功,后始省悟,自呼愚人不止,懊悔无及,如要卷土重来,非从民俗学入手不可。古今文学美术之菁华,总是一时的少数的表现,持与现实对照,往往不独不能疏通证明,或者反有牴牾亦未可知,如以礼仪风俗为中心,求得其自然与人生观,更进而了解其宗教情绪,那么这便有了六七分光,对于这国的事情可以有懂得的希望了。不佞不凑巧乃是少信的人,宗教方面无法入门,此外关于民俗却还想知道,虽是炳烛读书,不但是老学而且是困学,也不失为遣生之法,对于缘日的兴趣亦即由此发生,写此小文,目的与文艺不大有关系,恐难得人赐顾,亦正是当然也。
关于送灶
翻阅历书,看出今天已是旧历癸未十二月二十三日,便想起祭灶的事来。案明冯应京《月令广义》云:
燕俗,图灶神锓于木,以纸印之,曰灶马,士民竞鬻,以腊月二十四日焚之,为送灶上天。别具小糖饼奉灶君,具黑豆寸草为秣马具,合家少长罗拜,祝曰,辛甘臭辣,灶君莫言。至次年元旦,又具如前,为迎灶。
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云:
二十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枣栗胡桃炒豆祀灶君,以槽草秣灶君马。谓灶君翌日朝天去,白家间一岁事,祝曰,好多说,不好少说。记称灶老妇之祭,今男子祭,禁不令妇女见之。祀余糖果,禁幼女不得令啖,曰,啖灶余则食肥腻时口圈黑也。
《日下旧闻考》案语乃云:
京师居民祀灶犹仍旧俗,禁妇女主祭,家无男子,或迎邻里代焉。其祀期用二十三日,惟南省客户则用二十四日,如刘侗所称焉。
敦崇《燕京岁时记》云:
二十三日祭灶,古用黄羊,近闻内廷尚用之,民间不见用也。民间祭灶惟用南糖、关东糖、糖饼及清水草豆而已,糖者所以祀神也,清水草豆者所以祀神马也。祭毕之后,将神像揭下,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,至除夕接神时再行供奉。是日鞭炮极多,俗谓之小年下。
震钧《天咫偶闻》,让廉《京都风俗志》均云二十三日送灶,唯《志》又云,祭时男子先拜,妇女次之,则似女不祭灶之禁已不实行矣。
南省的送灶风俗,顾禄《清嘉录》所记最为详明,可作为代表,其文云:
俗呼腊月二十四夜为念四夜,是夜送灶,谓之送灶界。比户以胶牙饧祀之,俗称糖元宝,又以米粉裹豆沙馅为饵,名曰谢灶团。祭时妇女不得预。先期僧尼分贻檀越灶经,至是填写姓氏,焚化禳灾,篝灯载灶马,穿竹箸作杠,为灶神之轿,舁神上天,焚送门外,火光如昼,拨灰中篝盘未烬者还纳灶中,谓之接元宝。稻草寸断,和青豆为神秣马具,撒屋顶,俗呼马料豆,以其余食之眼亮。
这里最特别的有神轿,与北京不同,所谓篝灯即是善富,同书云:
厨下灯檠,乡人削竹成之,俗名灯挂。买必以双,相传灯盘底之凹者为雌,凸者为雄。居人既买新者,则以旧灯糊红纸,供送灶之用,谓之善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