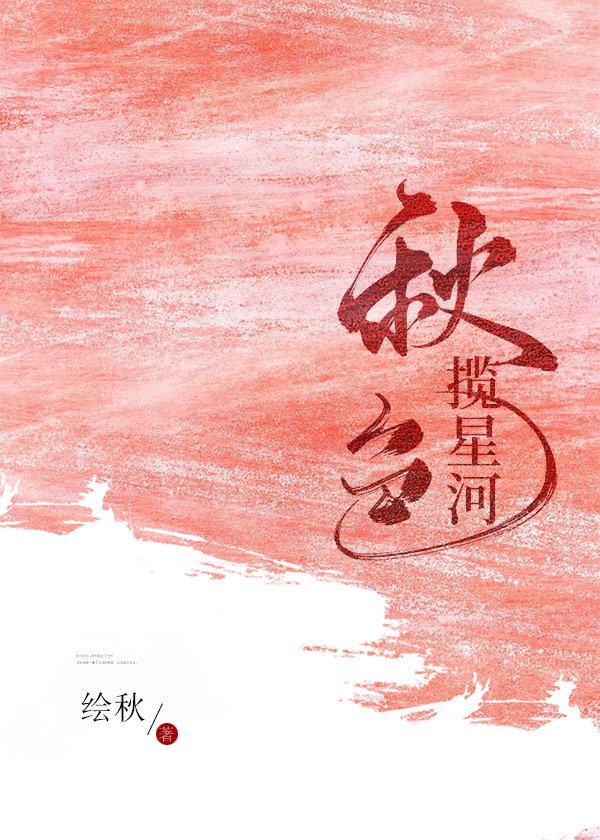六零小说>今天王爷想杀她吗 > 第80章(第1页)
第80章(第1页)
楚瑧垂着头没有言语,半晌才道:“小芙姐,我好怕他,他杀我父亲,害得我背井离乡,又辱我至此……”她颤声道:“我恨他!”
左小芙搂着她正要劝,却见楚瑧边擦泪边道:“可为了能回家,我什么都做,小芙姐,我该怎么做?”
左小芙自怀中掏出一本小册子翻开,道:“这是我这两个月搜集到的情报,慕容鸿除了可敦,还有三位夫人,这四人皆来自其他部落,身份贵重。先说可敦,她来自完颜部,十三岁就嫁给慕容鸿,但已多年不被召幸过,另外三个来自拓跋,贺兰和慕容本家,他最宠爱贺兰氏,这两个月里他召了十四次女人,光贺兰氏就七次,其他是另外两个夫人和侍妾女奴。”
楚瑧奇道:“小芙姐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?”
左小芙笑道:“每天晚上我可都去偷看呢,再找人打听打听就问出这些人的身份了。”
楚瑧有些羞,她觉得自己只知道哭,没派上一点用场,轻声道:“小芙姐,那怎么才能让那人……喜欢我呢?”
左小芙想了想,道:“这个贺兰氏十七岁,长得也不错,但根本比不上瑧儿,据说她未出阁时便爱同与人赛马打猎,从不服输,她本来是有婚约的,但慕容鸿喜欢她喜欢得不得了,硬是抢了过来,我还听说贺兰氏常常顶撞慕容鸿,但他从来不生气,或许就像贺兰氏那样张扬明媚的人才合他的胃口。”她顿了顿,道:“瑧儿,我想问问,那晚……你觉得慕容鸿对你是什么态度?”
楚瑧小脸一白,许久才道:“刚开始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,还笑了,可慢慢的就没什么兴趣了。”
“你有没有做什么让他不高兴的事?”
楚瑧道:“嬷嬷千叮万嘱,我就算再疼也不敢触怒他,一动不动,一点劲儿都不敢使。”
左小芙忽想到那夜打着打着慕容鸿都能起心思的事,一时无语,道:“我觉得他可能不喜欢温顺的女子,可能……越反抗他越兴奋吧。”
楚瑧弱弱地道:“小芙姐,那我怎么才能让他注意到我?”
左小芙想了想,和楚瑧嘀咕一阵,许久后,楚瑧双拳紧攥,沉声道:“小芙姐,我一定做到!”
次日,左小芙去找了那两个同她们一起干活的马奴,递上一包银子,道:“两位小哥,我家公主得了风寒,咳嗽不止,我得照顾她,这些日子的活计请二位辛苦些,我们每日少做两个时辰行吗?”
马奴掂了掂沉甸甸的钱袋,眉开眼笑,自然无有不应。
王庭外围一里处有片一望无际的湖泊,冬日结了厚厚的冰层,常有牧民来此凿冰钓鱼,亦有许多燕民在此嬉戏。其中一处稍远离人群的寂静冰面上,左小芙托着楚瑧的手在冰面慢走,后者穿的却不是普通的鞋子,而是底绑铁刃的冰鞋,楚瑧滑得摇摇晃晃,道:“这可比跳舞难多了。”
左小芙道:“瑧儿,你想让我放手吗?”
楚瑧犹豫了会儿,左小芙缓缓松手,楚瑧猛地把她的手抓回来道:“小芙姐,再……再来几圈。”
二人又转了几个来回,楚瑧便滑得有模有样,放开左小芙的手笑道:“小芙姐,冰嬉还挺好玩的。”
大齐贵族女子虽盛行小脚,但楚瑧说她母亲幼时吃足了裹脚的痛楚,便不舍得让爱女也如此,好歹留下一双天足。
“瑧儿,我们要日日练习,一个月里必须练得像模像样。”左小芙小跑着与楚瑧并肩道。
楚瑧点点头,又道:“小芙姐,要是可敦知道可怎么办?她肯定会阻拦我们的。”
“你放心,她没派人看着我们,这两个月里咱们一直乖乖的,她才没心思注意我们呢,一个贺兰氏都够她焦头烂额的了。”
楚瑧惊讶道:“你怎么知道没人看着?”
左小芙笑道:“要是有人监视我们,我肯定察觉得出来,小芙姐可是高手。”
楚瑧雪白的小脸儿被风吹得鼻尖通红,几丝鬓发发扬,她偏头去看左小芙,不妨脚下一滑就要摔倒,左小芙立刻抱她在怀,一点儿也没摔着她。
楚瑧仰头看着左小芙,一双大杏眸在冰天雪地中更显纯澈,她轻声道:“小芙姐,幸好有你。”
左小芙对上她的眼睛,满是对她的信赖依恋,不忍再看,转过头道:“今天……就练到这吧。”
夜里两人熄了烛火,躺在床上,左小芙忽道:“瑧儿,你白日说你母亲不舍得给你裹脚,她……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?”
楚瑧翻了个身靠近左小芙,搂着她的脖子道:“我母亲是天底下最好的人,她平常很威严,府里人人敬她,甚至怕她,听哥哥说在朝堂上那些大臣在她面前气焰也要低三分。母亲对哥哥也很严厉,可她在我面前总是很温柔,她最疼我了。”
左小芙盯着眼前的一片漆黑,半晌才轻声道:“是吗?我觉得我爹爹也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”
正月末,燕国的冰嬉之风达到了高潮,湖面上日日有赛事,惹得百姓围观,这日,慕容鸿自雪林间狩猎归来,见湖边人声鼎沸,不由得停了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