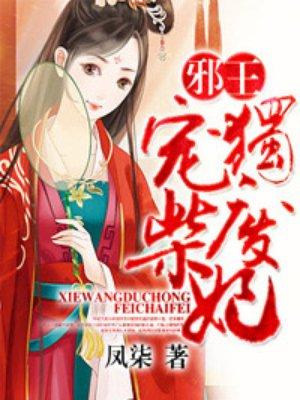六零小说>小青梅一直在解谜 > 向死而生(第1页)
向死而生(第1页)
牧晓说完,沉默了下来。
她没有去揣测对方听后的反应,也没去想这段话里的秘密万一对方泄露出去,会有怎样的后果。她只是静静地待在这份沉默中,似乎有人能倾听她说完这番话,就已然满足了。
过了不知多久,可能只是几瞬,也可能是半晌,她听到对面的人缓缓道:“我有些后悔。”
“不该用先帝的事,去激仁寿宫中在场之人。”这样只会把她的处境推到更危险的地步。
当日牧晞就是因此,才突然开始挑拨他们几个的关系——他发现,自己这妹妹,似乎也没想象中的那样信任身边人。
“还有,”苏墨清用略带疑惑的语气问她,“原来还可以更好么?”
牧晓抬头静静地看向他。
“如果你现在和过去,都‘不算全然真诚’的话……那我还得多加学习。”
“原来这样还算不够好么?”
“做到这个地步,都会问心有愧,都算‘无能为力’——我真的自愧不如。”
“我发现自己有个谬见。”苏墨清向前倾身望着她道,“我以为是我做了什么,让你一直觉得我想走,所以才用‘留’这个字。”
“现在发现,是自己会的太少,做得不够。”
“我该怎么办呢?早早掺上真心又如何,根本抵不过……”他突然很认真地转了个话头,“有人和你说过,在予人温情这方面,你当真厉害么?”
“少时挖空心思依旧不敌;现在还是不比你懂爱人之道。”苏墨清无奈地笑笑,“牧晓,这样会让我很期待。”
“原来还能更好么。”
“那我又该怎样留下你?”
牧晓怔了一下:“只要我还活着,就会一直在。你不需要……”
说到这里,她顿了顿,脸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笑容:“你也是这个意思。”
“自然。不过,”苏墨清缓缓道,“有一点还是不太公平。”
“你总让我们‘好好活着’,你自己呢?”
他伸手握住牧晓的左手腕,另一只手贴上她的掌心,垂眸道:“再早地旧账不翻了。就说从宫里出来那日,你回府要酒与冰,是想做什么?”
“你在西南经常这样做?”
“刚开始只是应急。后来呢?强迫自己清醒么?”
手中的指尖蜷缩了一下。他将那指尖轻轻抚平:“挑个不致命的伤口浸到酒中,会觉得畅快么?”
“我在担子最重的几个隘口,见过那样的神情。”
“明白自己总有一天会倒在一场冲锋中,所以能毫无波澜地浇上烈酒,再迎着寒风随意却克制地灌烈酒入喉。清醒,刺激,畅快,至情至性……不用去思索那个不知是否会到来的天明。”
“将生死置之度外,所以直面刀锋、勇往直前,向死而生。”
“但边军亦有轮岗倒班,戍期有定,有所期盼。”
“你准备就这样,一直到颈侧斫刀落下么?”苏墨清轻攥她的手,抬头问道。
牧晓释然地笑了笑:“对。这是我自己选的路。”
“我时常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痛苦。”
“但我一点都不后悔做过的所有。”
“也绝不后退。”
当朝皇帝登基之初,她缩在自己府中白白蹉跎岁月,渴望用掩耳盗铃、置身事外,换一世飘渺虚无的安定,一直在等一双能将她从痛苦中牵出的手。
后退再后退,放过再放过……但为何仍在失去,甚至连先帝在时,她都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的、挣扎反抗的力量和勇气,都一并放走了。